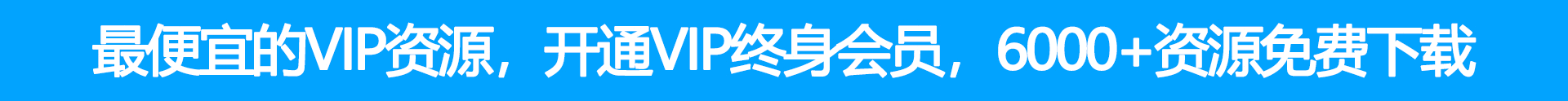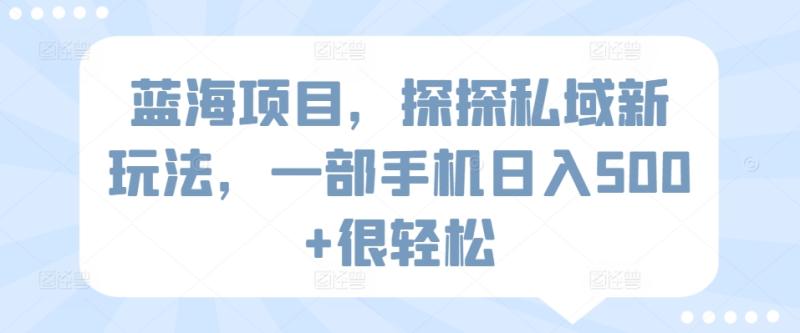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西学的性质,过去往往强调传教士传入的都是西方的旧学术,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四元素说”、盖仑的人体解剖学等。
而对西方近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波义耳的“新元素说”、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以及伽利略的实验法、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尔的演绎法等,或根本不提,或语焉不详。
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尽管囿于其宗教的世界观,传教士对一些西方当时最新的科学成就有所保留,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但其传入中国的不尽都是西学中的“古学”,其中也有不少“新学”的内容,如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就指出:“大多数人推测耶稣会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是陈旧的欧洲数学知识,然而只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才是如此·····耶稣会传教士所传入的不属于几何学的数学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
因此,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学应该说是一种新旧杂糅的混合体。实际上,当时传入的西学,不管是“古学”还是“新学”,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的学问,是性质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高势能的文化,这是无须回避的事实。
至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与当时中国占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相比较,则很难做出势能上的高低判断,但是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显然不同于中国的世俗文化,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高势能异质文化的传入,犹如在古老的中国文化深潭中扔下了一枚石子,激起阵阵涟漪。那精巧的自鸣钟、八音盒.五颜六色的玻璃珠、三棱镜,栩栩如生的圣母像,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以及《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奇器图说》《天主实义》等书籍,展示出了异域文化的风采,在中国的不少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明清之际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士大夫对其的回应具有多元的取向。这种取向大致说来可分为三大类:
一种是深闭固拒,完全反对,不仅反对“洋教”也反对“西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明代的南京礼部尚书沈碏、清初的杨光先,前者在明代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发动了“南京教案”,后者则在康熙初年挑起了“钦天监案”。
一种是广采博纳,全面接受,既信“洋教”亦崇“西学”,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如明代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但徐、李之接受天主教,主要不是出于神学信仰,而是力图以西方的“天学”来补充中国的儒学,所谓“补儒易佛”,即以天主教取代佛教。
第三种是有取有舍,取其“学”而舍其“教”,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取向,其代表人物如明清之际的方以智、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康熙帝等,他们之间对西学的取舍虽然还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基本主张却都是“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因此,这批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师夷长技”“中体西用”说的先行者。
由于清代自康熙朝以后的严厉禁教,西学在社会上的影响遂渐告衰灭。渐渐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愚昧无知,又回到了明末西学东渐之前,传统的“夷夏之辨”几乎又原封未动地被重新搬了回来,就好像持续了近200年的西学东渐在中国没有发生过似的,这看起来似乎荒唐的难以置信,但这确是真的历史。
第二期的西学东渐,一般认为是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正式开始的。但实际上,第二期西学东渐的时间还要稍微早一些,大致是从19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此期的西学东渐与前一期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传教士已不以天主教为主,而是以新教为主;其二,传教士虽然仍起到不小的作用,但其影响大大减弱,因为从这时开始,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主动去接受西学,即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追求。
第二期西学东渐,以1807年英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东来传教为其开端。当时,马礼逊原想在澳门登陆,然后到中国传教。但是,由于澳门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天主教徒反对新教,所以不允许他在那里传教。于是马礼逊只能前往马六甲,在那里专门从事写作。
他撰写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并第一次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后来相继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们,所用都是马礼逊的《字典》和《圣经》。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占领了香港,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开创之功,在香港专门建了一所马礼逊学校。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一批爱国的有识之士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将眼光投向域外的广阔世界,并激发了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打败侵略者的决心。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开其端,接着有魏源撰《海国图志》,以后又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等等,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种介绍西方各国地理、历史、政制的著作相继问世。
这一方面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当时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主动了解西方的一种思想转变和最初的尝试。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少中国人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物质科技的长处。于是,一批在政治上有力量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朝大臣,在既忧虑“夷祸之烈”,又痛恨“发(太平军)捻(军)交乘”的形势下,发起了所谓的“洋务运动”。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中国的日益深入,又由于洋务派办洋务之急需,再加上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日益迫切,“西学东渐”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唯一媒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通过传教士有选择地输入内容来窥西学之一斑,其遗漏、模糊甚至歪曲的情况可以想见。
但第二期西学东渐却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西学传播的渠道不仅有传教士的输入,有鸦片战争后私人的倡导和撰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由政府来主持这一工作。此外,西学传播的手段也已不仅仅是西书翻译一项,还包括了学校教育、新闻报刊的宣传和留学生及出使人员。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地来看一下这几方面的情况。
1. 新式学堂出现: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1863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以后各种新式学堂相继出现并不断增多,如“天文算学馆”“西学馆”“实学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等。这些都属于宣讲“西学”的新式学堂,其教学内容包括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矿物、天文、医学、军事技艺,以及各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富国策(经济学)等,所谓“由洋文而及诸学”。
此外,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一些西方的教会就纷纷到中国的那些通商口岸来开办教会学校,这也属于当时时髦的新式学堂。据统计,1876年,这类教会学校有350所,学生总数5975人;到1889年,学生总数已超过2万人。以上这两类学校,前者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后者带有明显的买办性和宗教性,但它们对西学的输入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
2. 西书的翻译大量出现并不断增多:洋务派对翻译西书十分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制造(即造船、造枪炮)之根本”,而且不必事事都“假手洋人”。在洋务活动中译书比较出名、质量也比较高的当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该局于1868年设立翻译馆,参与其事的人,中国方面有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西方人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
这些人的名字大家可能不是十分熟悉,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变迁的实际作用,绝不亚于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们所翻译的书籍,一开始集中在制造业方面,后来渐渐扩大到一般的自然科学方面,乃至少量社会科学方面,其中涉及的学科有:数学、测绘、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医药、博物、工艺、军事、历史、教育、政治、财经、外交等。据统计,到1880年,他们共翻译出版西书98种,未刊者尚有45种,到1879年,共销出31111部,计83454本。
当时,北京的同文馆也翻译了一些西书,其中著名的人物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把京师同文馆称作“译员学校”。目前所知此馆翻译西书有36种,其中外国教习译著14种、中国学生译著11种、师生合译7种、不详者4种。
同文馆的译著数量尽管不多,但质量却很不错,如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顿的《星轺指掌》、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塞特的《富国策》,都在其列。
此外,那些外国教会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还在通商口岸建立了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也翻译了一批西书,其中最出名的教会出版机构当推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和“广学会”。总的说来,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中,西方著作见诸中国译书目录的共达1442种之多,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广泛,均非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所能比拟。
当时翻译的西书以科技书籍为主,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它们属于非常普通而不是先进的,但在中国科技十分落后的当时,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有巨大的贡献的。当时属于社会或人文学科的书籍不多,但即使这不多的书籍,对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3. 报纸杂志的出现:报刊宣传是传教士在第二期西学东渐中的一个新的重要手段。早在1815年,马礼逊和另一名英国传教士米怜就在马六甲发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来华的传教士还在通商口岸办了一些报纸杂志,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从1815年至1890年,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共有76种,其中约一半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
这些报刊除宣传宗教外,还介绍一些西方的声、光、化、电之学。在教会或传教士办的报刊中,最有名的是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由林乐知任主编的《万国公报》(初名《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
《万国公报》以时事为主,介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对中国人了解中外大势曾起过不小的作用,特别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很多中国人从中汲取思想。另外,由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则是中国近代第一种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
4. 留学生与出使人员对西学的传播:1872年至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建议下,由容闳等率领,清政府派了120名10岁到16岁的学童分4批前往美国留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这是中国政府首批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他们之中出现了后来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
从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向欧洲国家派出了学习军事及航海、造船等方面的留学生,他们之中出现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杰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还有在甲午战争中英勇作战、以身殉国的邓世昌、林泰曾等人。
这些留学生,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西方严格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和传播西学方面是功勋卓著的生力军。此外,随着洋务活动的展开,中国大门被打开了,清政府也被迫要办理外交事务,并且派一些官员出洋考察。
自从1866年清廷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即参观考察起,派员出使考察也成为当时西学传人的一个途径。1877年,总理衙门奏准,出使各国大臣必须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记载,按月向总理衙门汇报,并将翻译外国书籍和报刊一并咨送。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曾纪泽、郭嵩焘、薛福成、刘锡鸿等人的出使日记,把他们身处异邦、耳濡目染的感触及复杂的心态,生动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些人写出的出使日记或游记,作为他们对外国的直接见闻及观感,对于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有一定帮助。
在1877年至1887年总理衙门奏定的《出洋游历人员章程》中,更进一步规定:“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力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该员如有曾经留意及出游之后能于性情相近者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这样,出国人员学习西学,便从制度上得到鼓励。
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维新思潮的鼓荡下,西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新气象。
1895年以后,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一大批学堂、学会、报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尽管绝对数量还不能算多,但比起以往的几十年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当时传播的西学,早已不仅仅是西方的自然科学,更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甲午战争后,许多热血青年纷纷自费赴日本留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的热潮。他们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探究一下日本“富强之本末”,他们通过日文转译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对传播新的社会改良乃至革命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到20世纪初,清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变法和“新政”的上谕,不得不承认清朝的洋务运动失败:“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连一直坚持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唯有行“新政”才能收拾清王朝残局,这证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具有不可逆转性。
第二期西学东渐在规模、内容上都要比第一期来得既深且广,但更不能同日而语的却是其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第一期西学东渐的社会影响面十分狭窄,主要局限在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以及少数开明的士大夫中间。而耶稣会士在民间的传教布道活动,也因当局的多方防范掣肘与中国百姓的普遍冷漠排斥,而无多少实绩可言。
所以,一旦清朝皇帝龙颜不悦,传教士就不得不乖乖地卷起铺盖走人。中国人心目中西学的那一点点微弱的痕迹,便迅速被湮没在岁月的积尘之中,重归于漫长的沉寂。而第二期西学东渐是在英国人的军舰和大炮护送下卷土重来的,其声势一开始就大不同于第一期。
在老大帝国脆弱的藩篱被摧枯拉朽般地撕破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较量,并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相对“高势能”而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
在这一期中,情况已经不再是中国皇帝用什么手段、在什么时间来遏制或驱逐西方文化,而是中国的百姓在怎样的现实教训、理智态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前提下,去逐步地、有选择地、有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期西学东渐本身,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极其复杂的作用。
经济领域中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政治领域中维新变法和革命,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怀疑乃至否定,社会结构领域中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上种种,都与这第二期的西学东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近代开始,西学东渐,新旧激荡,中国人从对西方文化茫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吸收西方文化。当戊戌维新变法之际,湖南有个顽固派人物曾廉,曾经这样概括过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三部曲”,他说:“变夷(向西方人学习)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
曾廉所说的“技”,就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言技”则是指当时的“船坚炮利”之议,即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李鸿章语),这是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
曾廉所说的“政”,就是指政治的“政”,而“言政”则是指早期改良派强调的议会政治,即如郑观应说的:“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君民一体。”这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
曾廉所说的“教”,就是指教化的“教”,即关涉到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素质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而“言教”则是指康有为在发动戊戌维新运动时在思想理论上做的宣传,即他发表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以为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叛逆”,这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吸收了西方进化论以后的状况。
以后,梁启超又比曾廉更明确地划分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中国人认为自己“从器物上感觉不足”;
第二期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中国人认为自己“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第三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人认为自己“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以上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的“三部曲”,是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近代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吸收西学的过程。从近代西学传入的内容和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阶段来看,确实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但还应注意到它们三者之间也不是绝对的,其间仍有互相交叉传播的情况,只是各个阶段的重点不同罢了。
第二期西学东渐,给近代中国以极其深广的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西学东渐密不可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简单地归纳一下:
近代中国人首先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实用价值,由此得出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生产技术的结论。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为中国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开始有了新式的军事工业;从70年代开始,有了新式的轮船公司,以及一系列用西法生产的工矿企业。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相应地要求交通运输、商业、金融等部门的近代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西方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引进,既为经济领域近代化所要求,也是为它服务的。由于这一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一些大城市原来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逐渐改变成为同业公会和商会等近代工商业的纽带。
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学,逐渐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推进,戊戌维新的变法运动是他们追求政治近代化的一次集中的实践。在此之前,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院制度的鼓吹,为维新运动的兴起做了舆论上的酝酿。
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直接推动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投身于变法的实践中。戊戌维新虽然被顽固派所扼杀,但维新派所传播的西学影响却极其广泛和深远。
在此之前,中国人大多还仅承认西学中的自然科学比中国先进,而认为在整体上中国文化还是比西方优越。但戊戌维新之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感到中国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文化。这就大大加速了辛亥革命到来的步伐。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学习西方表现出比维新派更大的自觉,也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他们从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找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探究建立共和国的方案。以后新生的共和国取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固然是国内诸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西学影响下才能够实现的。
判断西学对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经济和政治领域复杂得多。从大的方面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最典型的如对传统重农轻商、重义轻利观念的怀疑和否定。
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的许多士大夫已经不再耻于言商言利,反之却是对发展中国实业的高度重视。如咸丰状元孙家鼐创办广益纱厂,同治状元陆润庠创办苏伦纱厂,光绪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例证。西学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乃至官员选拔制度。古老的书院和科举制度最终让位于新式学堂,但最重要的还在于思想领域的革命,随着西学传播的深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从维新派开始,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们开始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学等所谓的“国学”进行再探讨,试图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当时这种体系按梁启超的话说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尽管有新旧拼凑之嫌,显得杂乱、粗糙,但却是一种新的尝试。
此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还初步提出了“道 德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民权思想、进化论等新的学说理论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广泛传播开来。
从人的角度来看,在19世纪后期,经过近60年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终于造就了一个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的是从传统科举道路中走出来投身近代化事业的,但更多的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学教育的人。
这群知识分子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对西方文化和知识的认识要深入得多,许多人已经开始以西方文化来对照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反思。正是这一代新的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开始承担起时代的使命,为不久到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必要和重要的准备。
如陈独秀发出“吾人最后之觉悟”的呼声就是典型的一例,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如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
正是有了这代知识分子的“最后之觉悟”的心理铺垫,五四运动时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才能向“孔家店”发起进攻。
然而,即使是这代知识分子,仍然很难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阴影,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先生的《彷徨》就是例证: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总之,几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外来文化输入中国这样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才能使之由外在变为内在,才能逐步与本土文化相贯通。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很多,最关键的是两点:
其一,是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贯通的主体;其二,是要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并加以培植和灌溉。所以,明清西学东渐的历史,今天对我们来说仍不失其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