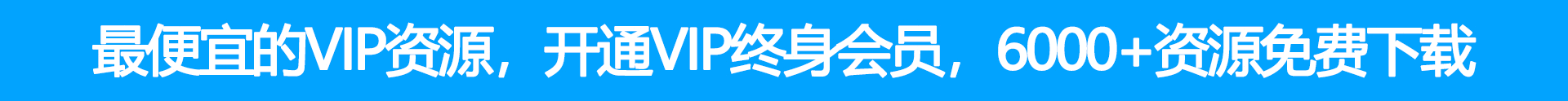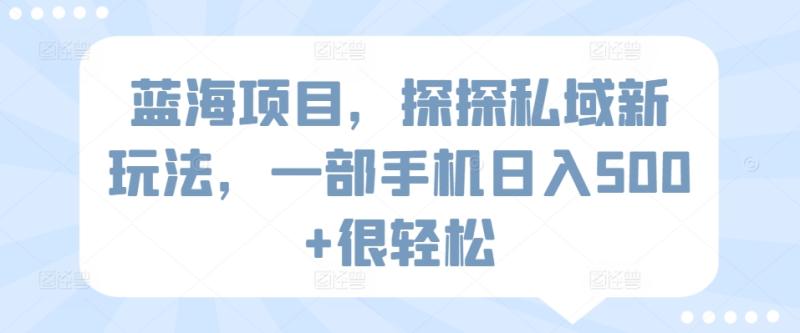眺望古越藏书楼
范玲玲
一个平常的下午,预报有雷雨的天突然放晴了,太阳是个好脾气的主妇,留了几丝清凉,沁人肌肤。
我站在灰白的门楼下,看古越藏书楼洗去铅华的真实模样。木匾上的字虽经红色描摹,仍然难掩疾风苦雨肆虐的痕迹。白墙下一溜青苔,像被时光腌制的写意画。门楼里面,歪歪斜斜地歇着一辆自行车,高起的门槛之间铺了水泥或木板,造成了一个个平滑的斜坡,便于电瓶车进出。我在门楼抚看的片刻,就有几辆电瓶车嗖嗖出入,骑车人昂首抬目,各有美好的愿景。
我在门楼里走了几个来回,尝试体会彼时国人的心境。门楼很高,白墙黑木,狭窄幽深,感觉自己好像从一个沉睡已久的梦里走了出来,猛一抬头,看见外面的天空,那么高远辽阔,于是用力地吸了一口空气,须臾,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我想,这就是徐树兰先生当时的心境。在一个黑暗的笼子里待得久了,连呼吸都被忽略了,有一天惊觉心中那股浩气是可以抵达青冥、瞩望胜境的。
徐树兰,优雅而深沉的名字,浪漫而务实的君子,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暗黑的中国撕出了一道光亮。
他是有钱的:父亲经商致富,他蒙受祖荫,衣食无忧。他是有闲的:光绪二年中举,被朝廷授予兵部郎中,因是武职,捐钱为候选知府,被用为盐运使,后母病回乡,不再出仕。他是有情趣的:读书吟诗作画自娱,以购书、藏书、印书为乐事,山水学文徵明、沈周,花鸟有恽格之秀。他是有理想的: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改革教育、务农富国,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和《农学报》,与胞弟徐友兰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良种,开辟种植试验。
彼时的绍兴,文化泱泱,藏书楼棋布林立,南宋陆游之父陆宰的双清楼、陆游的老学庵,元代杨维桢的铁崖山楼,明代祁承业的澹生堂、祁彪佳的八求楼、徐渭的青藤书屋、陈洪绶的七章庵,清代章学诚的滃云山房、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周星诒的瑞瓜堂、李慈铭的越缦堂、姚振宗的师石山房……可谓代有传人,各领风骚。
一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时时震荡在徐树兰先生的耳际:“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书与学便如蜂蜜与蜜蜂的关系,滋养者源源不断,受益者学无止境。
徐树兰先生选址于绍兴府城鲤鱼桥附近的古贡院,购地1.6亩,耗银32900余两,建造古越藏书楼。书楼共四进:三进是楼屋,供藏书用,书柜全系上好樟木制作;一进为大厅,挂有白底黑字的“诵芬堂”匾额,黑漆柱上是蔡元培撰写的劝学抱联,可以容纳60人看书,设有升降机方便取书。各进之间隔以天井,以利采光,天井铺以平坦而宽阔的石板,植有两株桂花树。当时人谓“花香伴随书香”,唇齿生香,心旷神驰。
楼成后,徐树兰先生在他私藏的基础上,捐银8600余两,添购当时中外新著,共7万余卷,并拟制《古越藏书楼章程》。他提出“存古开新”的主张,以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凡今籍分已译、未译二部,已译者供现在研究,未译者供将来研究及备译”。藏书有中国古籍和西方新书,有新学、农学、自然科学,有图书、报刊、标本、仪器等,首创中西结合的藏书体系,开拓图书分类技术的革命。古越藏书楼还接受社会人士捐寄书籍,图书在好学之士传阅,文脉在代际之间延续。
这就是古越藏书楼的开天辟地之功,这也是徐树兰先生思考一生、福泽天下的最大贡献。他说:“人才之兴,必由学问,学问之益,端赖读书。”他要为购书无资、入学无门的读书人提供求学的机会,他要施行文教而使中国强盛。北京的“北四阁”重门深锁,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亲自订立藏书族规,如“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女子不得上楼、外姓人不得入阁,即使是维新派办的藏书楼,也只对学会会员开放。那是传统的藏书楼,秘而不宣,子孙独享,宁喂蠹鱼也不示人。徐树兰先生此举,在黑暗、封闭、窒息的旧中国,无疑是一束光、一扇窗、一缕空气……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古越藏书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一别中国古代“以藏为主、以藏兼用”的理念,提倡“藏用结合、以用为主”。无怪乎1904年藏书楼对外开放,绍兴城为之轰动,读书人奔走相告。十年后,办公共藏书楼和图书馆蔚然成风。
书楼辅翼教育的硕果之一便是绍兴府学堂,或者说,绍兴府学堂也是书楼的源头。徐树兰仿盛宣怀所创天津中西学堂规制,创办绍兴中西学堂,适逢蔡元培痛心维新失败而弃官归乡,立即聘其出任总理(校长)。蔡元培招揽“极一时之选”的教员如鲁迅、徐锡麟等推进新式教育,增设日文、测绘、物理、化学、体操等科目,使绍兴府学堂成为清末国内新学堂的佼佼者,俊才迭出,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出版家胡愈之等。
想当年,蔡元培伴读徐树兰侄子徐维则,博览群书,学问大进,后受聘绍兴府学堂总理之初,创立“养新书藏”图书室,向学生及公众开放。这些书像浸润生命的最初河流,引他时时回望、刻刻徜徉,沐浴身心、充实肺腑,终以北大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理念润泽后人,绍兴府学堂成了今日的绍兴一中,延续了北大的博雅传统,从小地方走出去,成就大气象。可以说,绍兴府学堂和养新书藏是古越藏书楼的两大源头。
从绍兴府学堂走出去的徐锡麟偕陶成章、龚宝铨借毗邻古越藏书楼的绍郡中西学堂旧址创办的大通学堂,成了培养军事人才、推翻衰朽清朝的基地。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败就义,秋瑾在大通学堂被捕牺牲。那是炸裂清末铁幕的第一声锐响,穷千年之力量,迸青春的热血,让历史目眩良久。
另有有趣的掌故。五四运动先锋之一钱玄同和徐树兰的孙女徐婠贞结婚,七年后,徐婠贞在古越藏书楼后进的徐宅生下第四子钱秉穹。钱秉穹在北京读书,与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和有文学天赋的李志中要好,秉穹体格强壮,志中清癯瘦削,顽皮的周丰一各送“三强”和“大弱”的外号。钱玄同听后激赏,改名三强,寓意德智体俱佳。这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三强。
我期待着更多的一中学子走出绍兴古城,期待着更多的游人走进大通学堂。无论是教育或革命救国,还是科学救国,其根脉都在古越藏书楼,这一粒开放的种子吹开去,开了花,启蒙了人心,催生了思想,延续了文脉,开创了格局……
藏书楼开办八年后,辛亥革命的火种遍燃中华,徐树兰先生早已去世,临终嘱托儿辈办好书楼。徐树兰次子徐尔谷游宦离乡,书楼暂时停办,徐树兰之孙徐世南重开藏书楼,后其游皖再度停办。抗战时收为公办,改名绍兴县立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易名鲁迅图书馆,终定名绍兴图书馆。伴随国运的浮沉,还有令人扼腕的痛笔。张元济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古越藏书楼的五十余橱书奠定了最初的基本藏品,惜在日寇飞机对其的大轰炸中化为灰烬,片纸不存。文化总是被暴力欺凌,然而种子的力量是坚韧的,是绝处逢生的,它看得见千载而下纷纭之后的真相。
我又一次走进门楼,踏进古越藏书楼的遗址,昔日的阅览大厅如今成了一块空地,只有地上的长条石板还在提示从前的身份。各种野草填满了石板缝隙,围墙上蔓延着爬山虎铁黑弯曲的尸骸,各家各户种的丝瓜、四季豆占据了空中到处乱拉、随处可见的晾衣绳和电线。两条黄狗冲我嚷嚷,主人是个和颜悦色的老人,我顺着他的指点进了门楼左首的阅览室,登上木梯二楼,一个长形小间,总共七人看报,两位头发全白,我进去,没见谁抬头,只闻翻动报纸的窸窸窣窣,好一方净土。过了一会儿,一个戴布帽子、披防晒衣的女子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立时和一个男子聊起了股市,墙外就是胜利西路,市声喧嚣,我在这股凌厉的声流中探出了脚,走下了咯吱作响的木楼梯。
我从门楼下走出来,站到马路对面,眺望门楼的格局,黑白灰,简洁凝练,庄重自持,一棵很高的树垂向门楼一边,用它稀疏的枝干向门楼致敬。新和旧、老和青、居家生活和世外净土平和共存,互不相扰。一切都很自然,正是宇宙中最浑然的秩序。或许有一天,彼此发生了兴趣,可能会有新的天地开辟出来。
想今时,徐树兰先生日日坐在绍兴图书馆的广场上,左手握书,右手搁膝,神态安详,目光如炬,透过沧桑望穿千秋,遥想他从酝酿藏书楼的那天起,就一直在眺望中国的未来。而我,注定在他身后默默眺望,他开创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我的时代,我但求化身为他身边的一株绿草,聆听种子自由激昂的脚步,体味藏书清芬而深沉的气息。